, ]2 J0 {2 x# _0 ]: t* b. q' P7 D
林家翹,1916年7月7日生于北京,原籍福建省福州市,美國應(yīng)用數(shù)學(xué)家、物理學(xué)家、天文學(xué)家。林先生1937年畢業(yè)于清華大學(xué)。曾在中國清華大學(xué)、美國加利福尼亞理工學(xué)院、布朗大學(xué)等校任教。對(duì)近代應(yīng)用數(shù)學(xué)和流體力學(xué)的發(fā)展做出很多貢獻(xiàn)。2013年1月13日去世。
1939年林家翹與郭永懷,錢偉長等共21人同期考取庚子賠款留英公費(fèi)生。因第二次世界大戰(zhàn)突發(fā),船運(yùn)中斷,改派加拿大。本來,輪船將途經(jīng)神戶,日本在護(hù)照上簽證準(zhǔn)許登岸游覽。公費(fèi)生一致認(rèn)為,抗日戰(zhàn)爭期間,有失國體,故全體憤然離船,返回昆明。直到1940年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(xué)深造,1941年獲多倫多大學(xué)碩士學(xué)位。1944年獲美國加州理工學(xué)院博士學(xué)位。1953年任麻省理工學(xué)院教授,1966年當(dāng)選為全學(xué)院教授。林家翹是美國科學(xué)院院士,曾獲該院應(yīng)用數(shù)學(xué)獎(jiǎng)金(1976年)和美國物理學(xué)會(huì)第一個(gè)流體力學(xué)獎(jiǎng)金(1979年)等。從1947年起,歷任麻省理工學(xué)院副教授、數(shù)學(xué)教授、學(xué)院教授、榮譽(yù)退休教授。自1951年起成為美國國家藝術(shù)和科學(xué)院院士,1958年當(dāng)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,1962年起成為美國國家科學(xué)院院士。1994年當(dāng)選為中國科學(xué)院外籍院士,1987年清華大學(xué)授予他名譽(yù)博士學(xué)位和名譽(yù)教授,2001年11月被聘為清華大學(xué)教授。

年輕時(shí)的林家翹
林先生是國際公認(rèn)的力學(xué)和應(yīng)用數(shù)學(xué)權(quán)威。20世紀(jì)40年代開始,他在流體力學(xué)的流動(dòng)穩(wěn)定性和湍流理論方面的工作帶動(dòng)了一代人的研究和探索。他用漸近方法求解了Orr-Sommerfeld方程,發(fā)展了平行流動(dòng)穩(wěn)定性理論,確認(rèn)流動(dòng)失穩(wěn)是引發(fā)湍流的機(jī)理,所得結(jié)果為實(shí)驗(yàn)所證實(shí)。他和馮.卡門一起提出了各向同性湍流的湍譜理論,發(fā)展了馮.卡門的相似性理論,成為早期湍流統(tǒng)計(jì)理論的主要學(xué)派。從20世紀(jì)60年代起,他進(jìn)入天體物理的研究領(lǐng)域,創(chuàng)立了星系螺旋結(jié)構(gòu)的密度波理論,成功地解釋了盤狀星系螺旋結(jié)構(gòu)的主要特征,確認(rèn)所觀察到的旋臂是波而不是物質(zhì)臂,克服了困擾天文界數(shù)十年的“纏卷疑難”,并進(jìn)而發(fā)展了星系旋臂長期維持的動(dòng)力學(xué)理論。在應(yīng)用數(shù)學(xué)方面,他的貢獻(xiàn)是多方面的,其中尤為重要的是發(fā)展了解析特征線法和WKBJ方法。在數(shù)學(xué)理論方面,他也有些貢獻(xiàn),其中最突出的是他證明了一類微分方程中的存在定理,用來徹底解決海森伯格論文中所引起的長期爭議。他是當(dāng)代應(yīng)用數(shù)學(xué)學(xué)派的領(lǐng)路人。在美國有人將林家翹譽(yù)為“應(yīng)用數(shù)學(xué)之父”,有人說“他使應(yīng)用數(shù)學(xué)從不受重視的學(xué)科成為令人尊敬的學(xué)科。”
林先生對(duì)中國科技事業(yè)十分關(guān)心。自1972年以來曾多次回中國作學(xué)術(shù)訪問,邀請(qǐng)眾多美國知名專家來華講學(xué),接受多位學(xué)者去美國麻省理工學(xué)院深造,為國內(nèi)培養(yǎng)了一批有造詣的學(xué)者,推動(dòng)了應(yīng)用數(shù)學(xué)與流體力學(xué)的許多新領(lǐng)域在中國的發(fā)展,為中國科技事業(yè)的發(fā)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(xiàn)。2002年8月回國定居清華大學(xué),為中國教育事業(yè)的發(fā)展和清華大學(xué)創(chuàng)建世界一流大學(xué)勤奮地工作。
林先生曾擔(dān)任美國數(shù)學(xué)會(huì)應(yīng)用數(shù)學(xué)委員會(huì)主席、工業(yè)和應(yīng)用數(shù)學(xué)協(xié)會(huì)主席。他曾獲得美國機(jī)械工程師學(xué)會(huì)Timoshenko獎(jiǎng),美國國家科學(xué)院應(yīng)用數(shù)學(xué)和數(shù)值分析獎(jiǎng),美國物理學(xué)會(huì)流體力學(xué)獎(jiǎng)[3]。
林家翹先生是應(yīng)用數(shù)學(xué)家,他的地位和聲望是在不斷與難題挑戰(zhàn)中建立起來的,他與爭議有“不解之緣”。 林家翹先生的博士生導(dǎo)師是馮·卡門,他既是美國航空工程界的首席領(lǐng)導(dǎo)人,也是應(yīng)用數(shù)學(xué)及力學(xué)界的大師。他交給林先生的博士論文課題就是世界有名的一個(gè)多年有爭議的課題。這個(gè)課題是當(dāng)年物理學(xué)家海森伯格博士畢業(yè)做的論文題目,但許多人對(duì)海森伯格的研究結(jié)果產(chǎn)生了嚴(yán)重的爭議。馮·卡門有一位密友叫John Von Neumann,是近代最有名的應(yīng)用數(shù)學(xué)大師、美國原子能委員會(huì)委員,他在數(shù)學(xué)領(lǐng)域的應(yīng)用有多方面的貢獻(xiàn)。例如,他提倡用數(shù)學(xué)方法進(jìn)行天氣預(yù)測,最突出的是他發(fā)展的一套數(shù)學(xué)方法可以應(yīng)用到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領(lǐng)域,他手下的John Nash得了諾貝爾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獎(jiǎng)。就在林家翹先生畢業(yè)的那一天,馮·卡門請(qǐng)林家翹和John Von Neumann一起吃飯,將這位應(yīng)用數(shù)學(xué)家介紹給林家翹,希望他們之間能進(jìn)行合作。后來,Von Neumann就領(lǐng)導(dǎo)一組有名的學(xué)者,用計(jì)算方法證實(shí)了林先生的研究結(jié)果,結(jié)束了學(xué)術(shù)界這一多年的疑案。當(dāng)時(shí)林家翹做的這一課題是一塊難啃的硬骨頭,林家翹通過自己的研究,證明了海森伯格的研究結(jié)果基本是對(duì)的。于是,海森伯格就寫信給他的導(dǎo)師,說有爭議的問題其實(shí)是對(duì)的,是一位中國人證明了他的研究結(jié)果。為此,年僅30歲的林家翹先生就謀到了美國麻省理工學(xué)院副教授的職位。之后,林家翹繼續(xù)在湍流理論研究方面探索,沒想到在研究過程中與一位瑞典力學(xué)家各執(zhí)一詞,相同的問題研究結(jié)果卻相去甚遠(yuǎn),這位瑞典力學(xué)家為此在一次與別人的爭執(zhí)中得腦中風(fēng)而亡。林家翹在他去世前曾去醫(yī)院看望他,對(duì)他講,復(fù)雜的問題自然會(huì)有爭議,不是你研究的結(jié)果與我的不一樣你就不對(duì),其實(shí)兩人都對(duì),復(fù)雜問題是多方面的,不同的研究結(jié)果可以應(yīng)用到不同方面。他們這一學(xué)術(shù)理念最后變成了一個(gè)大題目——復(fù)雜性。有一種雜志專門取名為《復(fù)雜性》,對(duì)此類問題進(jìn)行探討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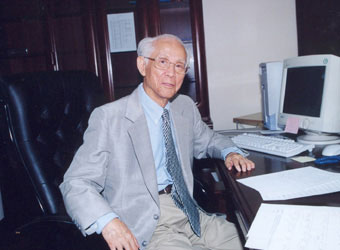
晚年時(shí)的林家翹
林家翹說,曾以工科成就享譽(yù)世界的MIT,如今在理學(xué)領(lǐng)域突飛猛進(jìn),生物等學(xué)科的發(fā)展水平更是令人刮目相看,所以和MIT的交流應(yīng)該理、工兼重,理學(xué)方面尤其應(yīng)該予以重視。林家翹說,“和國外名校交流時(shí),最重要的就是認(rèn)識(shí)彼此的優(yōu)勢和缺點(diǎn),取人之長、補(bǔ)己之短?!碧^注重實(shí)用性、以為“走在尖端和前沿”就是要引入先進(jìn)技術(shù),這是一種可能陷入短淺片面的看法。原則上先進(jìn)科學(xué)應(yīng)當(dāng)與先進(jìn)技術(shù)并重,但此中比例分配是一個(gè)比較難決定的問題。因?yàn)檫@個(gè)決定要基于國家需要以及人才物力和財(cái)政資源的實(shí)際情況,而這種情況也隨著時(shí)代變更。林家翹引用中國導(dǎo)彈專家梁守盤院士的觀點(diǎn)來作說明:“如果掌握了基本知識(shí)、知道了是怎么一回事,那么即使沒看到人家的技術(shù)細(xì)節(jié),自己也能通過想像把它做出來?!绷窒壬鷱?qiáng)調(diào),校際交流時(shí),應(yīng)該明確“想了解的知識(shí)”(what we want to understand)和“想制造的東西”(what we want to make)之間的區(qū)別。關(guān)鍵性的技術(shù)可能很難獲取,但基礎(chǔ)知識(shí)則是公開的,無需龐大的資金、人力投入就能走得很深。而“更要緊”、更能帶來長期效果的,也恰恰是基礎(chǔ)科學(xué)的交流學(xué)習(xí)。當(dāng)然,自己首先要“練好內(nèi)功”,達(dá)到能與國際同行平等對(duì)話的程度,交流合作才能順利進(jìn)行下去。
林家翹說,MIT的“全校必修課”是一個(gè)不妨參考的制度。在MIT,所有學(xué)生第一年必須全面學(xué)習(xí)數(shù)理化生4門基礎(chǔ)科學(xué)的知識(shí)。“中國的教育很早就開始突出專業(yè)性,MIT的全校必修課則是先廣再深?!绷旨衣N說,哈佛大學(xué)、布朗大學(xué)等名校普遍采用的“訪問委員會(huì)體系”(the Visiting Committee System)。這是一個(gè)沒有資金往來、純以領(lǐng)域?qū)跒楹献鳁l件的體系,目的是邀請(qǐng)其他高校的學(xué)者來參與相關(guān)建議、評(píng)估指正問題。當(dāng)年,林家翹自己就曾應(yīng)哈佛大學(xué)邀請(qǐng)加入一個(gè)10人左右的“訪問委員會(huì)”,為該校應(yīng)用科學(xué)領(lǐng)域的發(fā)展建言獻(xiàn)策。林家翹認(rèn)為,也許不一定要完全照搬這一模式,但請(qǐng)校外學(xué)者客觀審視相關(guān)領(lǐng)域的教研工作,這個(gè)思路是值得借鑒的。